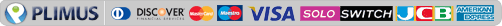|
花阴 一种手机监听的暧昧的隐喻 “花阴,即女阴。”荒木经惟在解释自己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作品集时如是说。荒木将借花隐喻的艺术表现手法并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他之前有意大利女摄影家缇娜·莫多蒂(Tina Modotti)、美国女画家乔治亚·奥基弗(Georgia O'Keeffe),之后有中国摄影家王小慧。与女艺术家以花的形态来展现女性器官借以张扬女性个性、表现两性平等的诉求不同,作为男性的荒木表现出更多的只是一种窥视的欲望。
旅德摄影艺术家王小慧与“花之灵/性”主题作品 花与女性始终是艺术的重要题材,直白地以观花的形式完成对于女阴的窥视也绝非现代艺术的创见。北宋小清新晏殊在一首《渔家傲》中写过“醉折嫩房花蕊嗅。”的露骨句子,花的子房与女性乳房、花蕊与女阴呈现出赤裸裸的对应关系。由于花与女阴在形态和生殖功能上的相似性,花几乎存在于每一种文化的自然崇拜与生殖崇拜过程中。 如果说类似《诗经·庸风·桑中》“爰采唐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这种男女欢好场景的描写充满了诗意与暗示,那么少数民族民俗仪式则直白了许多。清人屈大钧在记述早期两广文化的《广东新语》中写到:“越人祈子必于花王父母。有词云白花男,红花女,故婚前亲戚皆往送花。”作为古越人后裔的壮、侗、瑶等民族都存在兼有自然崇拜与生殖崇拜的花崇拜文化。广西龙胜的红瑶小寨敬奉生育女神花婆,红瑶民歌《十二月怀胎父母》云“小妹当昔得一梦,梦见南海金树泓;小妹当昔摘一朵,戴起头上满头红;庆见摘花一个月,就是儿子上娘身;左手摘花是男子,右手摘花是女人……”,红瑶族认为生育是花婆摘花送人引起的,女阴即为“花”,而阴蒂就是“花蒂头”。在红瑶族文化中阴蒂与生育息息相关,若不想生育便以尖利的竹针刺破阴蒂进行流产。 红瑶家称女儿为“红花女”,别家的女儿何尝又不像花一样柔软美丽。花在自然崇拜中是生殖的象征,绽放与凋零不过失生殖任务的进度条。为了完成繁衍生息的自然使命,花进化出各种各样的形态、气味来吸引能够帮助他们授粉的生物。女为悦己者容也为使人悦己而容,虽然动机并不纯粹是为了完成自然使命,但这种行动本 身就足以让人产生繁花般香艳的联想。
荒木经惟的作品 荒木经惟所拍摄的花阴就是利用了这种联想。无论是用亚里士多德的类似联想、洛克的观念联想还是休姆的相似联系或是其他联系的分类方法,花蕊都在形态和功能上与女阴存在相似之处。一朵花在未完全建立性观念的孩童眼中大概只是一朵花,即使放大局部、缩短观赏的距离都不会改变他对于花的认识。处于禅宗青原行思说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第一阶段,对于现代人而言这一阶段不会太长,绝大部分人终其一生都将处于“看山不是山”的第二阶段,即便在其性欲消亡、生殖功能解除后仍是如此。
荒木经惟作品 色情与写生可能仅仅存在着角度上的差别。荒木的拍摄花几乎不需要对花本身进行修饰,他需要调整的只是自己。由于荒木择取的角度,成人很难摆脱联想在脑海中单纯地还原一朵花的形态。荒木将画面背景设置成黑色,只有彩色的张开的花朵是有色的、招摇的,和他拍摄涩谷街头的女人一样,张开了身体的每一个毛孔等待被液体浇灌。 花朵美好的自然形态间接为释放人类社会普遍观念对于窥视女阴这一带有色情意味的 行为的压抑提供了出路。肉欲倘若是不是毁灭自己的欲望,至少也是寻求刺激和无保留地放纵自己的欲望。色情生活是人类行动力与能量的来源,然而它的表象是肮 脏的,这为蔑视色情提供了令人心安理得的理由。如果对这种表象进行否定并宣称本性中没有任何肮脏的东西,又会流于庸俗。性欲本身会有如此肮脏,如此危险、 如此模糊的因素,人们接触它的时候无法不加倍警惕、拐弯抹角。花在“零落做红泥碾做尘”前,可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除了巴西雨林里的大王花,多也是“暗香浮动月黄昏”清新淡雅。只要观者能道貌岸然地正襟危坐,把持住自己不让手伸向蠢蠢欲动的下体,头脑中的淫魔乱舞又有什么关系。
荒木经惟作品 植物将自己的生殖器毫不犹豫地暴露着,像发情期的动物一样勃起着、炫耀着,这简直是阳光下最难容的罪恶,然而大多数人都觉得花朵很美;人们用手、唇以及其他 能够带给自己感官刺激的器官去抚弄花朵,除了以性冲动来解释人类行为的心理学家和符号学家,很少有人会将之视为性欲的发泄。人们看花、爱花都无涉色情,但从荒木的镜头中看花便色气满满,倘若王守仁也从同一视角看花,心学大师内心的花开花落会颜色会不会也一时明白起来?
荒木经惟作品 荒木在他作品观众的脑海中植入了一个危险的概念,花阴即女阴,这种概念植入的冲击力与毁灭性比《东京喜乐洞》(Tokyo Lucky Hole)强烈得多。英国美学家爱德华·布洛在《作为艺术因素与审美原则的“心理距离说”》中指出,距离太近会使人们斥责某一艺术作品为粗鄙的自然主义, 令人难堪,咄咄逼人的现实主义。《东京喜乐洞》是那种距离太近的作品,感官刺激强烈,和动作爱情片一样刺激着发泄欲望的本能,但不美。朱光潜先生认为作者创作色情作品、受众主动接纳作品如果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那就和肚饿吃饭、体冷穿衣一样,“只是使用的活动而不能算是美感的经验”。对着“露白蒹葭而外”的美人“动”了三十九次的金圣叹将好色好淫与情、礼绑定,“好色与淫相去则又几何也耶?若以为发乎情,止乎礼,发乎情之为好色,止乎礼之谓不淫。”以 花阴代女阴而以镜头窥探之,止乎于礼,因而不算淫,由于发乎于情,荒木的《花阴》与《花曲》两部作品集也不会是单纯的自然写真。英国律师蒙哥马利·海德在为色情作品辩护时说“艺术作品如果没有涉及性方面的、表现普通人性的东西来赖以生存的话,它不可能获得真实,更不可能流传。”所以花阴与女阴等同的危险概念仍将伴随着镜头的延伸不断祸害一代代纯洁的心灵。
荒木经惟作品 在内心禅定之前再也不能直视花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