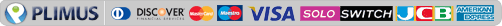符合程序的,是否就一定是正义的?
泄露美国监视项目最高机密信息的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近日的行动,强烈地冲击了“程序决定正义”的政治道德。斯诺登对美国政府以维护公民安全的名义收集数以百万计美国人电话记录和恐怖主义嫌犯互联网通信信息的权力感到不安。 斯诺登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表示:“我想让香港法庭和民众决定我的命运。”
“我有许多机会离开香港,但我宁愿呆在这里,在法庭上与美国政府斗争,因为我对香港的法治有信心。”
对公民来说,恐怕也有必要在遭受如同厦门公交车爆炸案那样的无妄之灾和让渡部分隐私之间交出自己的道德选项。未来很长时期内,关于国家权力与个体权益之间如何平衡,关于国家利益与全球正义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将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新课题,斯诺登不过撕开了一道口子。
《南华早报》头版的最新专访中,斯诺登更是爆料称美国政府已入侵中国大陆与香港特区的网络多年。他向媒体公布证据,表示美国政府网络入侵中国网络至少有四年时间,美国政府黑客攻击的目标达到上百个,其中还包括学校。
斯诺登此举给两国首脑刚刚“甜蜜”会面的中美关系出难题。斯诺登表示他的举动“不是要逃脱正义,而是要揭发罪恶”,但他却已陷入罪恶与正义的囚徒困境当中:背叛他与美国政府之间的保密协议,对获得授权的政府权力日益扩张感到愤愤不平。“背叛”成为了通向他认为正义的行动的必经之路。
根据现实的法律系统,斯诺登恐怕难以逃脱美国司法部门的控罪,而鉴于香港与美国签订的引渡协议,斯诺登恐怕也难以如愿以偿地获得他期待的“庇护”和“全球正义”。但理论上,斯诺登对美国政府的发难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来监督“监督者”?当公民对地方正义表示不服从和质疑时,谁是全球正义的裁判?
这涉及共同体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争论。共同体主义更相信,政治道德的根源在于共同体的存在,共同体主义不期待世界主义的普遍道德为共同体内部的成员提供道义的外援。而世界主义则相信一个更为普遍的政治道德的存在——地方正义之外,全球正义更符合人类道义上的福祉。如果承认共同体正义的价值,那么,斯诺登的行为背叛了他对共同体的承诺,与他达成协议的共同体有理由宣告他的背叛是不正义的,但看起来不幸的是,斯诺登似乎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相信全球范围内,总会存在同情他的普遍道德和全球正义。
这似乎只能从“9•11”恐怖袭击给美国公民乃至全世界带来的巨大不安全感说起。基于防范恐怖主义袭击的需要,“ 9•11 ”之后,美国政府获得了一系列强大的监控权力,如恐怖袭击之后立刻获得通过的《爱国者法》(Patriot Act),就开始赋予了美国政府监听公众电话的广泛权力。
据《华盛顿邮报》和英国《卫报》报道,以反恐的名义,美国允许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和联邦调查局(FBI)搜集各种数据,这项秘密计划始于乔治•W•布什政府时代,代号为“棱镜”(Prism),始于2007年。最新曝光的内容则显示,布什时代的许多反恐政策在奥巴马任内是如何得以保留,甚至被加强的。欧洲媒体及美国媒体开始谴责奥巴马政府的全面监控策略做法“令人发指”。对此,奥巴马辩护说,“你不可能在保持百分之百隐私、保持零不便的情况下,获得百分之百的安全。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将不得不作出一些选择。如果你好好看一下具体细节,我想你会发现我们找到了恰当的平衡。”
的确,奥巴马说出了制约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安全之间的两难,至于政府方面是否做到了恰当的平衡,评价的权力似乎不应当在操纵者手里。也就是说,即便斯诺登对政府权力扩大和公民隐私遭到侵犯的反抗是违背他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契约的,即便他对权力的警惕是过敏的,对隐私保护是有洁癖的,他仍然在客观上充当了敲响警钟的批判者角色。国际社会如何评价斯诺登和他的行动,是一件极为微妙的事情。他究竟是反抗强权的公民英雄,还是背信弃义的叛徒?这取决于人们心目中的天平-----程序与正义、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如何倾斜。
其实,给斯诺登贴上什么标签并不是最重要的,世界各国的公民有比这更迫切的诉求需要被正视:在当下这个风险社会,个体的安全感是否越来越依赖于国家机器的强力保障,如果是这样,那么,公民如何确保自己由于日益依赖于权力的庇护而让渡的隐私权不受严重侵犯(奥巴马表示目前带来的影响是“对隐私的轻度侵犯”)?还有,谁来界定究竟是轻度侵犯还是重度侵犯?如果公民对轻度侵犯也感到不安呢?如果社会成员对是否基于安全的需要而让渡隐私权并未达成共识呢?再有,如果恐怖主义的蔓延是全球化的,那么,反恐是否也是跨越国界的,如何协调一种恰当的国际秩序来应对世界公民的安全需要?
这一系列问题,恐怕将会借助斯诺登案例使得“全球正义”再度成为学者们和政治家们争论的焦点。世界主义代表博格就曾经提出,只有通过改变全球制度规则,才能实现全球正义。共同体主义派内格尔的思想比较复杂,他认为可以通过不正义不合法的暂时性策略走向正义的社会:“全球正义最可能的路径是通过建立不正义和不合法的全球权力结构实现,那些结构容忍当前最强大国家的利益。只有以那种方式,为了更民主的目的,才能产生值得采纳的制度;也只有以那种方式,才会有某些具体的东西使合法性要求继续起作用。”他认为,“正义的全球范围将只有先通过增加世界的非正义来扩大,引入有效的但不合法的制度,正义的标准适用于这些制度,借助于那些标准我们可以最终改变那些制度。这也许是历史的可爱之处”。
“有效的但不合法的”,这样的措辞也许可能为斯诺登的违背契约和保密协议提供了道义上的辩护。而斯诺登选择中国的香港,也许正是基于对“全球正义”的迷信。需要审慎观望的是,这些偶发的或许史无前例的案例,将会给中美两国政府带来怎样的冲击和改变?如果维护公民安全的责任日益全球化,与此同时,公民对隐私权遭到侵犯的忧虑也同样日益全球化,那么,中国扮演怎样的角色,就成为了值得期待的事情:中国政府如何重新认识自己在世界格局当中被日益赋予的国际化角色?如何考量国家内政与全球正义的政治道德及其可能的张力?
当然,对公民来说,你恐怕也有必要在遭受如同厦门公交车爆炸案那样的无妄之灾和让渡部分隐私之间交出自己的道德选项。未来很长时期内,关于国家权力与个体权益之间如何平衡,关于国家利益与全球正义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将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新课题,斯诺登只不过撕开了一道口子,以非常规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了这一议题新的面向和可能。转载请注明出处